現代人好八卦,對於發掘古今名人的軼事、醜聞尤其感興趣,如愛爾蘭一代畫師法蘭西斯.培根,他的極端一生早在90年代成為大眾的談論對象,甚至被拍成電影,對其同性戀及虐待癖大說特說。
紐約書評評論人、著名藝術史家約翰李察遜最近舊事重提,本著史家的良心不談是非風月,反而憑當年的一段友好關係向世人重現他所識的培根,答案卻是:他(培根)並沒有那般出色!
法蘭西斯.培根(Francis Bacon)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,
父祖皆是名門望族的後裔,跟他同名的叔叔更是英國最著名的政治家及哲學家。他於1920年代末期開始繪畫,未受過正規的藝術訓練;1945年,他憑藉作品
《三幅十字受刑架上的人像習作》(Triptych: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
Crucifixion)參加倫敦拉斐爾畫展聲名大噪;他後來的《自畫像研究》(Study of
Self-Portrai)更成為了當代繪畫中的經典作品,並在1971年時被法國藝術鑑賞雜誌列為當時十大畫家之首,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之一。
儘管藝術成就驚人,培根的一生卻在憂鬱與不快中度過。
扭曲童年 易服成癖
據資料記載,培根少年時體弱多病,對動物患有嚴重的敏感症,因此自小便大量服用藥物,以減輕症狀;家族雖有名望,亦不乏兄弟姊妹(有一兄一弟,兩個妹妹),可是性格內向,與父親的關係亦不愉快。
因為個性羞澀,培根天生彷彿便跟同年紀的少年不相同,他舉止行為女性化,甚至喜歡易服變裝。他曾不
只一次在盛大的舞會上,穿上珠片閃裙,塗抹濃妝,將自己打扮成花枝招展的舞女;更有一次因被發現穿上了母親的內衣而被父親痛打一頓,但這些痛苦的經歷卻成
為了培根日後的創作泉源。
約翰李察遜(John
Richardson)最近接受《衛報》訪問時不忘透露對好友易服的觀察。約翰指出,培根家中年老的保母不時「鼓吹」培根的放縱行為,「她睡在廚房中,彷
彿無時無刻都為培根的偷竊行為──如他最愛的雜貨、化妝品及為讓頭髮定形的鞋油──大作掩飾。」李察遜繼續補充:「她又為培根提供不尋常的收入來源,每次
當藝術家們開非法的派對時,她都會在玩紙牌咭的人客堆中收到了大量的小費。」
李察遜甚至記述,他曾經在派對中聽聞培根對保母說,「他們(派對上其他的藝術家)應該留待至男男交媾的環節。」李察遜因此認為,培根不應被視為唯一沉溺同性愛的英國藝術家。
畢加索後有培根
85歲的年邁藝術史學家李察遜,一直以來以研究畢加索聞名,他於1991年出版第一部畢加索傳記而獲得英國的惠特貝瑞文學獎(Whitbread Prize),隨後在1996年、1999年分別推出第二、三部,使他在藝術界中享負盛名。
今年,他為紐約書評(New York Review of
Books)重新審視好友兼著名畫家培根的一生,他指出,培根的一生因其虐待癖相伴,培根在藝術上固然有卓著成就,但其末期的作品,卻因為欠缺了受虐的苦
痛而失去神韻,並不應如以往評論家般一味的讚嘆。李察遜在既有的評論上另立新意,因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。
險被男友打飛眼球
李察遜指出,兩個男友對培根影響最為深遠。培根的第一個男友彼德雷斯(Peter Lacy)猶如其父親的直接投射。他在父親日接夜的虐打中獲得了受虐的快感,而雷斯更可說是變本加厲。
在李察遜眼中,雷斯每每對培根作出「最兇狠的攻擊」;在長期的酗酒中,雷斯甚至曾經將培根整個人擲向房間的玻璃外,使他的臉部嚴重損傷,右眼更險被打飛,要靠縫針才可把眼球安放原位。
「但培根更愛他這個暴力的男友;後來弗洛依德(Lucian Freud)因得悉此事而對雷斯提出抗議,使他搬出了原來的居所,這促使培根與弗洛依德的友好關係破裂。」
但李察遜書中卻不忘提出雷斯帶來的「啟發」,「人所共知彼德雷斯在鎮上臭名遠播,他對待培根如奴隸,並不時對他拳打腳踢;不幸的是,這卻大大提升了他對愛人創作的靈感,使他畫出了最出色的幾幅作品。」
1954年,培根按照男友的形象畫出了《Man in Blue》系列,坐在垂直黑帳幔背後身穿黑禮服的兇惡男人,正是培根最「疼愛」的原型。
受虐爆發藝術靈感
但最為人認識的卻是培根在雷斯以後與佐治戴爾(George Dyer)的另一段關係。
1998年,英國導演約翰梅布瑞(John Maybury)憑電影《愛是惡魔:培根的自畫像》奪得了多個國際電影獎項,電影充滿性慾元素,講述培根如何誘導入屋偷竊的小偷戴爾發生關係,並在以後的日子成為他畫中的主要模特兒。
電影著力營造浪漫愛情故事,但在約翰眼中,二人的相處遠遠超越浪漫成份。
「培根曾承認他會用各種手段使戴爾精神上崩潰,然後到了每個最適合的清晨,他便會忘卻對愛人的所作所為,畫出他的巔峰之作。」
在1964至1974年的十年之間,戴爾成為了培根靈感的繆恩,他的畫作時而與愛人對話,風格逐漸傾向暴力、荒誕,用扭曲的面相與身體表現他內心的激情;通過畫畫,他思考人的存在,在戴爾自殺之前,他一度稱自己為存在主義者,更有「暴力是存在一部分」的名言。
屍體當模特兒
可是二人的關係並不長久。李察遜憶述1968年的一個黃昏,當他與兩人進餐過後,戴爾因一場爭執獨自離開。「過後,培根跟我通電,他說他的愛人倒在酒店房間門外,手中一大把的安眠藥及一樽威士忌,那時他已不醒人事。」
在首次自殺不遂過後,培根對愛人的逼迫愈來愈深;戴爾不久後在希臘第二次自殺不遂,最終在1974年於巴黎服藥身亡。
在戴爾逝世之後,培根陷入了極度的傷痛之中,但卻沒有令人忘記他曾在一次自殺事件中,依然拿著畫筆描繪出戴爾垂死的形態,此舉亦使大眾對培根作出了嚴重不道德的指責。
「所有我深愛的人都離我而去了,我無法停止想念,所以只能更專注於我的藝術之上。」培根在事後解釋說。
不是僥倖 便是災難
在佐治戴爾離世之後,李察遜認為培根作品的質素快速下滑,儘管他之後交了另一男伴約翰愛德華
(John
Edwards),但他與愛德華的戀情卻遠離了以往施虐受虐的情人關係,使他的作品再無生機。「在愛德華的影響下,培根的作品由魔鬼的形象淪為一般健壯男
子的裸照,然後他筆下那些充滿性暗喻、無頭無臉的男性軀體,慢慢轉變成了簡單的軟性情色畫。」
迄今為止有藝術館三次舉行培根的作品回顧展,最後一次是上年4月由泰德畫廊(Tate Gallery)舉辦的回顧展,現場出現的當代藝術家如Damien Hirst、David Sylvester在節目上一再肯定培根的名望,可是李察遜卻認為這一類評價失諸客觀。
「簡單來說他就是畫不出來,他無能為力清晰勾勒出所畫的對象及其空間,玷污了一幅又一幅的作品,他的『Screaming Pope』系列的成功不是一次極大的僥倖,便是一場重大的災難。」
培根於1992年去馬德里旅行的途中去世,去年佳士德的拍賣會中,他為紀念愛人佐治戴爾離世畫的名
畫《室內的三個人像》(Triptych, May-June
1973)以高價賣出,那是培根受苦最深時期的作品,模糊不清的人物在三個不同的空間展出頹廢的姿態,正是這惡魔畫師最得意的作品之一。
(原文刊登於2009年11月27日《文匯報‧博覽》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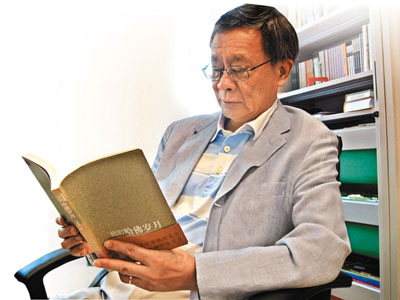



.jpg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