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有詩「狐狸何足道,豺虎正縱橫」,狐狸者,其狡猾、其不馴,自古以來少為人所稱道。
因此難以想像一學者以狐狸自況,旁人看來或以為是對自身惡意的嘲諷,就算不然,亦必帶點戲謔成份。如若不究因果,又何以得知李歐梵自稱狐狸型學者,原來已確切反映出他做學問的思想體系,乃至於其多年來面對學術、生活的一套價值觀?
由早年對五四文人的浪漫傳統及「現代性」、「後現代」思潮的探討,到近年電影、音樂、建築無所不寫,無所不談,冷不防還會跟周星馳來次「真情」對話,李歐梵身體力行告訴大眾,狐狸老矣,而他的人文關懷卻從不止息。
「狐狸的意義應當解釋一下。我的說法是,刺蝟型的人只相信一個系統,狐狸型的人不相信任何系統,比較懷疑。也就是說我不願意做一代大師,能自以為然地講出一套一套的。」──《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》
今年是李歐梵的退休年,中文大學的職務剛正式完結,他另一邊廂已為將於香港大學開設的六堂人文學科
講座密鑼緊鼓籌備中。這是李歐梵自2002年留港後第二次跟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合作,計劃是由傳媒學院主持,然而課程所涵蓋的五花八門,更是他積
累多年有關全球化下人類文化普遍面對的大議題;開課前他抽空跟記者一行人茶敘,也給了各人一份親筆撰寫的課程大綱:「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」、「重構人文學
科和素養」、「小說的當代命運」、「文學與電影:經典的改編藝術」、「聆聽二十世紀:音樂與文化」及「大都會中的田園:人文建築的風景」,猶如六道佳餚置
放眼前,我們笑說,每一道都足以成為一篇博士論文了─更要是來自不同範疇的六味上菜──可是對於向來眼觀六路,耳聽八方的李歐梵來說,這種博覽群(學)
「科」式的授學理念又有何出奇?
李歐梵對文化的熱忱,跟他的身世學養有直接關係。父母是音樂家,使他自小培養對西洋音樂的熱愛;在
大學時期,他就讀的正是台大外文系,他跟白先勇、王文興、陳若曦、歐陽子等人辦《現代文學》雜誌,後來眾人都紛紛邁向作家的路途,李歐梵卻沒有趨步而行,
相反一下子衝進了政治學的懷抱。「我當時想做外交官,覺得父母會以為文學沒用,做外交官反能賺錢。後來我卻失望了,因為我發現自己對政治完全沒興趣。」結
果到了1963年,李歐梵終於從芝加哥大學轉到哈佛大學的「東亞地區研究」碩士班修讀歷史,他回憶當時隨兩大學者費正清(John King
Fairbank)及史華慈(Benjamin
Schwartz)學習,對他啟發極深,尤其後者的辯證思維,更使他培養出做學問每事懷疑,凡問題都會反覆辯證澄清的「狐狸式思維」。
「大概是我入學後的第三年──我和費教授的關係開始接近起來。他公開稱我是一個「放蕩不羈者」(free spirit)……我從此也更以此自居,逐漸在思想上獨立起來。」 ──《我的哈佛歲月》
李歐梵或許情願打文化游擊也不願意做一代大師,然而八年的哈佛生涯卻成就了他學術上的地位。「在撰
寫博士論文時,費正清教授要我們寫一個人的傳記;當時五四無人寫,只有周策縱的一本《五四運動史》,我也寫五四,但覺得一個不夠,結果就寫數個作家,並從
徐志摩開始想『浪漫』的問題,究竟『浪漫』是一種心態、主義,還是個性,並將作品同文學史連繫起來寫。」結果他的博士論文《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》(後
編輯成書出版)成為了早期研究五四文學的學者不能不讀的論著;在輾轉「流徙」於政治、歷史的國度後,他重返文學的領域,撰寫於80年代的《鐵屋中的吶喊:
魯迅研究》沿夏志清的研究脈絡,將魯迅從政治上的「神」還原為「人」,開闢了以後「魯學」的新路向。
不過,既然是一個「放蕩不羈者」,又曾受學於多個學術領域,而且多年來行走各國如一「都市漫遊者」
(不正是他常掛於唇邊班雅明的Flaneur形象嗎?),可想而知,李歐梵絕不甘心只留守於文學領域──或者更正確點說,他更樂於站立在每項人文學科的邊
緣位置,由此不只充當起建構者的角色,也可不時對「主流」、「中心」展開批判,這在在成為了他對中國「現代化」/「現代性」問題的思想根據;亦因為他同時
對中、西文化的高度認知,使他能屹於高樓望東西,比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挖得更深,望得更遠。
「我要作一個像伊凡卡拉瑪佐夫一樣的知識分子!俄文intellignetsia這個字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。」──《我的哈佛歲月》
由台灣走到美國,由美國東岸走到西岸,最終在新世紀開展之際,李歐梵選擇了香港這彈丸之地開始人生
的另一章節。2004年初抵香港,那年他65歲,李歐梵笑說,這正是一般人的法定退休年齡。然而在這短短的七年間,他在香港卻宛若重演了前半生的教學生
涯,在香港中文大學出任只此一人的人文學部教授,輪流在文化研究、歷史、文學等學系講學授課,教導莘莘學子;直至今年正式退休,他不但應中文大學之邀在未
來兩年繼續任新書院晨曦書院的顧問教授,幫助建設外國小書院的教學精神,也應香港大學之邀參與人文學科錄像教學的計劃,希望能藉此將具深度的文化知識下達
學生、群眾,裨益社會。這一切一切,除了是本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,也建基於李歐梵終生不殆的人文關懷,而他與香港更有說不盡的情分……
(文:筆者 李:李歐梵)
文:你曾經說過,你與香港的因緣是基於妻子是香港人的關係;但就我觀察,香港對你影響甚深,甚至一般人以至學者都說香港不是好地方之際,為何你反而獨愛香港?
李:這出於一段奇怪的因緣。我記得1970年第一次來港教書便是在中文大學,當時有一個教授載我到尖
沙咀,我沿路看著建築物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,因為我很喜歡這種中西文化混雜的特質。在後來決定返港時,我就說我已是半個香港人。雖然到現在我仍
不是香港永久居民,但這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。對我來說,要做一處地方的永久居民就是對那地方要有承擔感。香港給我很大的挑戰,因為愈是資本主義,愈是商品
泛濫,我愈覺得自己有用,我很希望對香港有一點點的貢獻,尤其對如今這個過度商業化、過分官僚主義的社會有一點人文的影響,讓下一輩生活得好一點,我有這
種理想。
文:你一直很強調對人文(humanity)的關注,你是何時開始感受到這種嚴峻的人文危機?
李:也是在香港。2003年SARS時,全香港好像死了。什麼資本主義也好、動感之都也好,一個
SARS全都沒有了。那時候感覺人會把人文資源全拿出來,因為人快死的時候都會回想從前,可是香港人無法做到,因為香港人太注重「現在」,太重利益,因此
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沒有了,時間停頓了、城市也被封鎖了,我感受很深,那時候我就感受到被封鎖時人正正需要人文的滋養。
文:那麼對於重拾人文主義,你有什麼新的看法?
李:現在的時代注重現在、當下,事事要快,可是「慢」對我來說才是一個可供思考的空間與時間,人才能感受到這時代是怎樣的。這就已經是很大的人文危機,如果連我們這些人文主義者都沒時間去思考,問題如何能夠解決?如何面對挑戰?這些都是我現在細想的問題。
我有一個較奇怪的想法,就是將這個時代跟一百年前比較,可能當時會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陰影。由此,我
想到文化的靈魂,我想通過這種奇怪的比較方法,從以前不同的時代取用當時的文化,從而使人的精神、靈魂、文化生活豐富起來。因為任何一種文化背後都有所
本,有傳統、有回憶,但現在的人都認為人文主義保守傳統,沒甚可說,我就要看看有沒有新的方式去講,希望人能夠學懂將「日常生活」(everyday
life)豐富起來,可以抵抗過度的資本主義。
文:我可以說你是一個資本主義抵抗者嗎?
李:我不是激進批評資本主義的人,更應該說我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者。但我覺得不滿
(discontent)很重要。你對雷曼兄弟不滿,就上街去;對學校不滿就應去抗議。人需要不滿,太過滿足是不行的,尤其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,更不應對
現狀過分滿意,一定要對現狀不滿。我有時感到奇怪,現在中國人對現狀都是挺滿意的,年輕人覺得生活舒舒服服,中國強大富足,好像沒有什麼不滿,可是我作為
知識分子,就開始有點警覺了。我不是革命主義者,也不是改良主義者,我認為人,尤其年輕的,一定要抱有不滿,因為只有不滿才能產生思考的力量,才能產生想
改變生活的力量,不是說要成為社會上的異類,只是我覺得香港人太乖了。
文:你會繼續留在香港嗎?你以後的學術路途又如何?
李:我現在也有想這個問題,很矛盾。我一方面希望做研究,一方面又希望做小文章,所以我也在做一個最
大的決定:我將來要做什麼?如果做學術,我就一定會到台灣;香港這個社會的好處在於多元化選擇,可是這地方太侷促了,沒時間思考。我自己很有罪疚感,因為
作為學者,我做的研究不足。雖然寫過許多書,但都是只有普通的學術價值,《上海摩登》算是比較好的,但我認為自己仍未寫出一本有份量的大書。所以我說,可
能到台灣一兩年,把書寫出來,也有可能不去台灣,這就是我的規定,如果留在香港就繼續寫小文章好了。
後記
「我曾跟朋友打趣說:別人一般講『文章是自己的好,老婆是別人的好』,我卻相反,『文章是別人的好,老婆卻是自己的好』。」
白先勇曾經說,李歐梵與李玉瑩的婚姻有如傳奇,是「半生緣」加上「傾城之戀」的;二人識於微時,成婚於晚年,李太太照顧了丈夫一生的「飲食」,李歐梵在太太憂鬱病患期間不離不棄;後來二人更合著了《過平常日子》,簡單五字道出了兩口子對生活的期盼。
「我老婆剛才離開,我們去了食午飯。」
因訪問之故,記者第三次跟李歐梵見面,時近中秋。
「我們還去了中國文化研究所猜燈謎……」李歐梵笑得眼都瞇起來了。
「結果是她猜中了……哈哈!」
我終究不知道那燈謎的內容是什麼,但我衷心相信與妻相伴是這浪漫文人最大的幸福。
(原文刊登於2011年9月18日《文匯報‧文化名人訪談錄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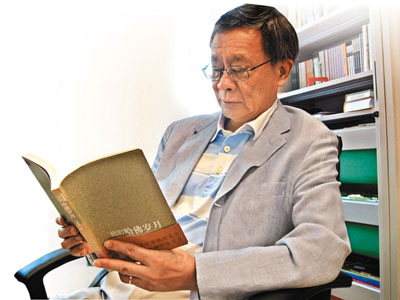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